那年秋收,整个村庄都沉浸在金黄稻浪的喜悦里。
叔叔永强魁梧如松,挥镰割稻,汗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我那时七岁,赤着脚在田埂上奔跑,捧着一瓢凉水,跌跌撞撞地喊着:“叔,喝水!”
他放下镰刀,一把将我举过肩头,笑声在稻浪上滚动。
婶子翠云站在田头,额发濡湿地贴在额角,笑容像秋阳一样暖:“慢些跑,小心摔!”
她递给我一块粗布汗巾,让我给叔叔擦汗。
那汗巾带着泥土与阳光混合的气息,包裹着最安稳的滋味。
她的笑容,是我小小世界里,最温润明亮的底色。
然而,冬意渐浓,北风呼号,吹得窗纸扑簌作响时,婶子眼底那层温暖的光泽也悄然褪去,仿佛被凛冽的寒气冻住了。
起初是细微的冷硬,像灶膛里偶尔迸出的火星。
我吃饭时不小心掉落一粒米,她眼神便如冰针扎来,声音低沉:“糟蹋粮食,眼睛长哪里去了?”
我怯怯地缩了缩脖子,不敢再动筷子。
叔叔放下碗,想说什么,嘴唇翕动了几下,最终只化为一声沉沉的叹息,像块石头投入寒潭,激不起半点暖意。
家里的空气,从此凝滞如冻土。
裂痕最终被一只小小的木马彻底撕裂。
那天,我在柴房角落玩耍,翻出一个粗糙但可爱的小木马——那是叔叔悄悄削磨,预备给未来孩子的礼物。
我欣喜地抱着它跑进堂屋,木马在手中快乐地颠簸着。
婶子正坐在灶前,昏黄的光勾勒出她僵硬的侧影。
她猛地抬头,目光像淬火的刀子,狠狠剜在我脸上,又死死钉在那只小木马上。
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一声爆响,火星飞溅。
她骤然起身,疾风般冲过来,劈手夺过木马,狠狠摔在地上!
木头碎裂的声音刺穿耳膜。
“谁让你动它的?
谁准你动的!”
她尖利的声音刮擦着四壁,眼中燃着疯狂的火。
我像被钉在原地,只能看着那只小小的木马身首分离,腿断成了两截。
恐惧凝固了血液,我忘了哭,只呆望着地上那团无辜的残骸。
叔叔冲进来,脸色铁青,一把将我护在身后,对着她低吼:“你疯了吗?
他还是个孩子!”
婶子胸膛剧烈起伏,嘴唇哆嗦着,像风中枯叶,却最终没再吐出一个字,只是死死盯着地上那堆破碎的木头,眼神空洞又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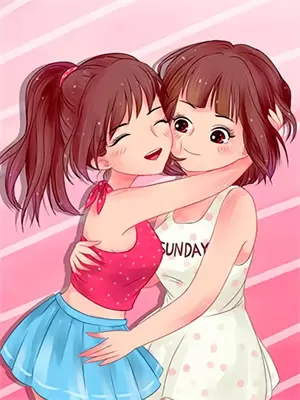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